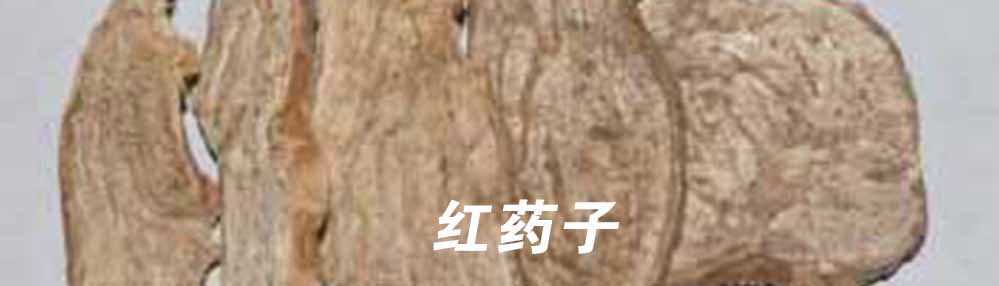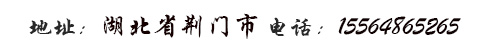白石道人的浪漫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
点绛唇姜夔丁未冬过吴松作!燕雁无心,大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姜夔的身份非常特别,他不是辛弃疾那样的沙场英雄,也不是如同苏轼的科举文臣,他既不会武功,也考不中科举,但却有极高的艺术才华,无论诗词书画,还是音乐棋艺,他的造诣都非常深。于是尽管没有官职,但他却深受士大夫高官喜爱,经常成为他们的座上宾,共同讨论切磋艺术方面的问题,由此,他也可以获得一些生活资助。于是姜夔的一生便游走于不同士大夫的府邸,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像姜夔这样的人在南宋其实数量不少,他们中有很多人就主动去士大夫家中干谒,并不期待传统的科举入仕,而完全将投赠诗书词画等艺术品作为谋生的手段。因与高居庙堂的士大夫相对,后世一般把这个群体称为江湖文人。姜夔在江湖文人群体中也显得十分特别,他颇以清高的风骨自期,不愿意过着摇尾乞食的干谒生活,而是要与士大夫平等交往。于是能和他们一样获得科举出身而有个官做,便是姜夔内心深处的渴望。只是现实过于残酷,他始终没有获得进士出身,而他的士大夫朋友也难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所以他一直过着清苦的江湖漂泊,也就留下了一些书写旅途寂寞的词。这首词姜夔记录了一次经过太湖第四桥的心情。湖边的山水一如他此刻的心情,满是烟雾迷离的清苦。第四桥边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故居,姜夔颇以陆龟蒙自比,如果不能仕宦,那么和陆龟蒙一样做一个湖山诗人也是不错的。但这个愿望也难以实现,因为他身无长物,根本无法像陆龟蒙那样买地建屋。心愿不能实现,却总是莫名在第四桥下经过,那他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将情绪洒在摇曳的秋柳上,感伤自己的无用。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姜夔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情人的分别,是人间最痛苦的事情之一,若是两情相悦,双方都得承受无比煎熬的寂寞相思。若只有一方痛苦相思,那便要承受更大的悲痛。因为想见又见不到,于是能在梦中见到也是一种安慰。但是梦中的场景往往缥缈虚幻,梦中人的面孔也相对模糊,还不如画像看得真切,思念者还嫌弃起梦境来了。嫌弃归嫌弃,他当然还是愿意在梦境里待更长的时间,于是当山鸟啼破了他的幽梦时,还是要对其责怪不已的。人便是如此矛盾的动物,处于深情状态中的时候,更加如此。然而情深并未影响他的思力,在长年漂泊,两鬓灰白之时,他突然悟到时间的无情,既可以衰老容颜,还能够冲淡情感。刚刚分别的时候,大家当然都痛苦得撕心裂肺。但是日子总得要过,也就强忍伤痛进入新的生活。当一切重新回到稳定的每日轮回,人也就逐渐接受分别的事实,甚至心中会有无法再见的预期,情感也就慢慢地变淡了。只有某些特定的时刻,才会突然激发已经藏于心底深处的思恋。一如此刻,正是元夕佳节,是家人团聚之日,也是情人约会之时。每逢此夜,看着别人家的欢娱与温馨,不知是谁就会悄悄地爬进我的心底,闯入我的梦乡,让我重温相思的苦痛。想来,自己也应该在这天晚上进入那个人的梦境吧。但除了她自己,又有谁知道呢?或许她早已把我忘记,正在苦苦思念另一个人吧。都说姜夔这首词追忆着早年在合肥的一段情事,这段与两姐妹之间发生的苦情,在二十年后依然让他念念不忘。或许并不一定要将词情如此地坐实,因为词人只用空灵清劲的语言,说了一段过往的故事,而这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位饱含深情之人的身上。杏花天影姜夔丙午之冬,发沔口。丁未正月二日,道金陵。北望淮楚,风日清淑,小舟挂席,容与波上。绿丝低拂鸳鸯浦。想桃叶、当时唤渡。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兰桡、更少驻。金陵路,莺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姜夔十四岁的时候不幸丧父,不得不依靠姐姐生活,于是早年便在湖南湖北流寓,足迹甚至到达过江淮之间。二十八岁的时候,有幸结识了父亲的老友萧德藻。这位当时名气极大的诗人非常赏识姜夔,特地把侄女许配给了他。在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的时候,也就是词序中提到的丙午年,萧德藻被授予浙江州知州,姜夔随即决定举家跟随,来到了他生命后半段最重要的活动空间江南。现在,姜夔的小船摇到了金陵,正式进入了江南地区。小序说得很明确,他眼前的风景是清淑和丽的,但客船却在这美好的空间里徘徊不前,因为舟中人的心底产生了不知所起之情。全词开篇以金陵名胜桃叶渡起兴。不必深究有什么特定情事,毕竟桃叶渡在词中过于常见,这里只是用典故带出不知所起的幽怨情绪,而下文突然转向小舟的徘徊无定,也足以说明男女情事只是点到而止的笔墨。金陵在南宋是行都,城市已经再次繁盛起来,于是姜夔在过片就用六朝往事描绘着此日盛景。但下接的“算潮水、知人最苦”一句又陡然将词人从风景中抽出,成为旁观风景的他者。如此一来,词情的苦恨就在男女情事之外增添了多种解释可能,身世况味、游子思乡等情绪也逐渐地生起。而结尾的前路迷茫的叹息又再次不将情感落实在某一特定的地方,只留下浓郁的忧伤气息。人生正如行旅,总会碰到像此词抒发出的这种情感。在它兴起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缕情丝,但在其流泻的时候却捕捉不到它的痕迹。就是自己也不能确定究竟产生了哪一种情绪,但却明明感到,某种情绪就在那里。扬州慢姜夔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扬州是隋唐时代著名的大都市,不仅经济发达,更是江南名流荟萃的地方,这里有层出不穷的才子佳人,流传下许多风流的故事。晚唐的时候,扬州城里最耀眼的风流才子是大诗人杜牧,他不仅在扬州的青楼巷陌间度过了一番自在逍遥的日子,还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将自己与扬州城浪漫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也让扬州成为每一个以才华自许的男青年格外向往的地方。姜夔当然也才华横溢,但是他在淳熙三年()来到扬州的时候,见到的却是与杜牧笔下不同的风景。宋室南渡之初,金人的兵锋多次攻陷过扬州,仅仅有明确历史记载的就有建炎三年()、绍兴三十年()、绍兴三十一年()、隆兴二年()四次,其间还遭遇过金海陵王完颜亮的大肆破坏,扬州城当然完全不再是那个富贵风流的名都,而变成了只留有断壁残垣的边境小城。不仅如此,身处扬州的姜夔也与当年的杜牧心态完全两样。杜牧来到扬州的时候,刚刚考中进士,同时也考取制科,正处于“两枝仙桂一时芳”的春风得意。而他在扬州,更是担任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掌书记,具备少年才子之外的无量前程。然而二十来岁的姜夔来到扬州的时候,却是一无所有,没有中举,没有官职,没有知音,更没有未来的希望,他来这里,只是为了寻求一些生计。于是,这首词中的国仇家恨还带着身世浮沉的况味,所以才会如此凄怆。全词大量使用对比的修辞。起首三句,铺陈扬州往日壮丽,紧接着,就着力描写现如今的种种萧瑟荒凉,乱离之象与不堪回首均跃然纸上。下阕转入对于杜牧的设想,如若杜牧英魂旧地重游,一定也会为眼前的荒凉感到震惊。尽管姜夔化用了许多杜牧的诗句,但并不一是因为他要以杜牧相比,而是通过重新展现杜牧文字中的扬州风流,再次与今日的荒寒萧瑟形成对照。如此,才能凸显兵荒马乱之后山河破碎与人事飘零,才能让萧德藻体认到浓郁的黍离之悲。淡黄柳姜夔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因度此阙,以纾客怀。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桥宅。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姜夔的词往往会有一段优美的小序,将词作的写作时间、地点以及所要抒发的情绪先行告知,然后便只在词中塑造冷峻凄清的意境,内心情绪则力求不露痕迹地表现。这首词便是这样的典型。根据词序中的交代,姜夔当时居住在合肥。南宋的时候,江淮之间的合肥正是与金人作战的前线。与姜夔后半生的主要活动空间江南大为不同,这里当然不会有京畿的那种繁庶,只有凄凉冷清的巷陌。于是词的第一句也就有了落脚点,角声是极富边关色彩的元素。人世的沧桑总是会被无情草木衬托出来,此刻也是如此,姜夔发现合肥柳树并不在意是否身处战乱,依然年年抽条长叶,一片繁茂,与江南细柳同样令人迷醉。当人在异乡发现与故乡相似的风景时,自然会勾起一阵浓郁的客愁,而姜夔尽管并不生在江南,但综其一生,还属江南时光较为潇洒惬意,可以向士大夫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从而将其认作精神上的故乡,因见柳树而思念,也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既然见到了与江南差近的柳树,又适逢清明寒食的季节,那不如按照江南习俗,去郊外冶游寻春,偶遇一段浪漫的邂逅。但真的这样做了,才会发现这里毕竟不是江南,而是萧瑟的空城,飘零之悲一下子又浓郁地升了起来。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合肥的春日如此凄清,但毕竟还是春色,总没有秋日那么寂寥。但仔细想想,就是这样的春天似乎也不长久。柳条早已由黄变绿,更到了随风动的季节,这意味着春日已深,来日无多了。当梨花落尽的时候,就将变为一片秋色,这看似无理的词句其实暗示着人心已入秋日,流寓边关空城的自己将行至迟暮的年纪。飘零与迟暮,构成了序文中的客怀。这不仅是姜夔这样的江湖清客的哀怨,也是南宋初年时刻担忧战乱的人们共同的忧愁。暗香姜夔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咏物词非常难写,特别是已经被前人反复吟咏过的事物,如果不能翻出新意,便会落人俗套,也就没有什么艺术感染力。姜夔的这首《暗香》提示了一种经典手法,就是讲一个与这件事物有关的情事,由于事件的唯一性,会让词中的事物超凡脱俗。这两首词名为《暗香》《疏影》,显然得名于“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句诗。这是北宋诗人林浦《山园小梅》一诗的名句,姜夔的两首词也就在吟咏梅花。但是他一开篇就借月光与梅花将思绪引入了无限的回忆。梅边吹笛是过往的欢娱,他用精妙的笛声唤来一位佳人与他共赏雪月之梅,真是一段风流浪漫的故事。而“几番照我”一句又早早地告诉大家,这样的夜晚其实是曾经的日常,在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何逊而今渐老”一句,用何逊的典故将时空转回当下,而今不仅人散天涯,自己也年华老去,才力消退,再也演奏不出当年月下梅边的清曲,只是暗自惊怪,窗外的梅花怎么又开了?其实吧,玉人不再的时候,哪里还有兴致去填词吹笛呢?那些文字与旋律,就是给她看给她听的,也只有她才能知晓个中深趣呐。过片依然停留在当下时空,抒发路遥难寄相思的情感。旧时的梅花依然绽放得那样美丽,尽管无言沉默,但也在追忆那远去的佳人。于是“长记曾携手处”一句又将思绪拉回过去,拉回到那片倒映着千树梅花的西湖。但“又片片”一句再次悠悠地将思绪拉回现在,佳人与过往都如同此刻被片片吹落的梅花瓣,再也见不到了。尽管并没有描摹梅花,但全词就是笼罩在一片梅花的清冷幽香之中。疏影姜夔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宮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这首词与上词连缀而下,却讲了另一番故事。《暗香》的最后说到梅花被片片吹落,《疏影》开篇即从一瓣梅花落英讲起,让它在时空隧道中往返穿梭,展开了一段奇妙之旅,极似不断切换的电影镜头。这片花瓣的旅程从一株枝头出发,那里有一只会幻化为绿衣女子的青鸟,正在沉沉睡去。花瓣与它轻轻告别,飞到了一片篱笆旁,有一位佳人倚靠着修长的绿竹,不知道在守望着什么人。落日的余晖打在她的脸上,将她映衬得更为孤独。离开了这位佳人后,花瓣莫名地飞到了茫茫大漠见到了憔悴思乡的王昭君,此刻的她身处荒寒,尽管无比思念江南的温暖,但却不得不接受永远回不去的现实。只能期待逝去后的芳魂能够飞回故乡,哪怕化作小溪边的一树独自开放的梅花,也已足够了。用王昭君来比拟梅花,虽不是姜夔原创,但怎么想都有些牵强,很可能是因为姜夔将家国之恨融入了词中,想到了沦丧的中原,与客死北国的徽钦二帝。当然,这样的情绪就算真的有,那也是点到为止。花瓣在下阕继续旅行,似乎真的接着昭君寄寓的家国感伤,它开始在宫殿中游走。先到含章殿下欣赏寿阳公主娇媚的睡姿,又去汉武帝为陈阿娇打造的金屋,然后便和其他落梅一起掉入了御沟水流中,伴着哀怨的笛曲《梅花落》,顺水漂向了遥远的地方。最终,它飞上了一幅精美的图画上,结束了这场旅行,至于伙伴们都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暗香》《疏影》是姜夔最负盛名的词篇,若说《暗香》借讲一个故事寄托自我孤独憔悴的身世,那么《疏影》更多是利用这段旅程,展现了此际破碎的山河。图片来自网络,赏析来自陈引驰读古词。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ongyaozia.com/hyzyll/10560.html
- 上一篇文章: 天涯诗友总期期尺幅素宣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