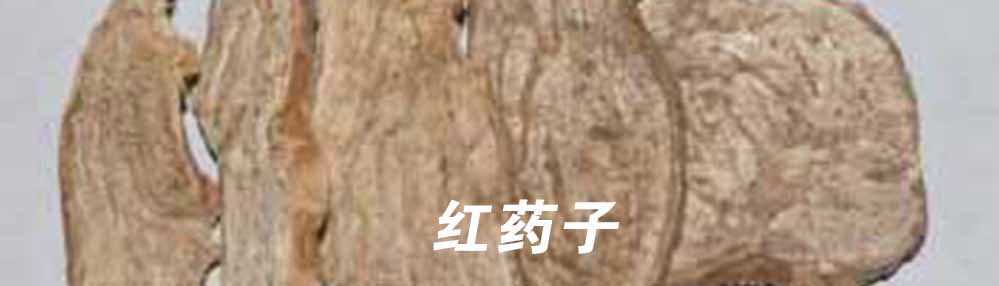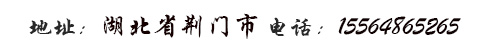李运富杜甫名句ldquo朱门酒肉臭
|
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训解疑难二题 李运富 (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河南郑州) 摘要:杜甫诗句“朱门酒肉臭”,其中的“酒肉臭”应指酒肉变质变坏,一般解为发臭。“香气”说提出质疑:一是“肉可臭,酒能臭吗”?二是杜甫之后有不少诗作用过“酒肉臭”,有些“臭”只能解释为“香”或“香气”,那杜甫诗句的“臭”也应该是“香”。其实“酒肉臭”是“酒败肉臭”的并言省文,并不存在“酒可臭吗”的疑问;后世的“酒肉臭”确有应该理解为“香气”的,但应属误解杜诗而产生的仿用,不宜反过来证明杜诗的“酒肉臭”也是“香气”。 关键词:杜甫;酒肉臭;并言省文;误解;仿用 杜甫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是杜甫描述沿途所见所闻后对当时权贵与平民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揭露,并非特定的实情实景。 其中的“臭”就意义解读而言有四种说法:一指腐臭难闻的气味或形容臭;二指变质腐烂;三是泛指气味;四是特指香气或形容香。处于对立状态的是臭气(臭)与香气(香),对立双方各有理据,尹戴忠、赵孜在《语文知识》年第1期上刊发《“朱门酒肉臭”的“臭”字释义争议及辨正》,对双方各种观点作了梳理,并站在“臭气”方立场对“香气”方的各种质疑逐一辩驳,结论是“臭”仍当为“腐臭”之义。但此后的争议并没有停止,双方仍在继续申述各自的理由。比如最近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就又提出《“朱门酒肉臭”中的“臭”字怎么读?》(中华读书报),根据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所引《艺文类聚》的语句渊源,以及当时的生活真实和杜甫诗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认定“‘朱门酒肉臭’中的‘臭’字还是解作‘发出臭气’较为妥当”。可“香气”方仍然不肯接受,又引起一轮争议。主要有两个质疑点还没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一是“肉可臭,酒能臭吗”?二是杜甫之后有不少诗作也用过“酒肉臭”,其中有些“臭”只能解释为“香”或“香气”,那杜甫诗句的“臭”不也应该是“香”吗?这两个问题确实厉害,解释不圆满,就难怪别人不服。 一、“酒肉臭”实为“酒败肉臭”的省文 杜甫诗句属于用典,典源见于《艺文类聚·人部八》引王孙子《新书》[1]: 楚庄王攻宋,厨有臭肉,尊有败酒。将军子重谏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尊酒败而不可饮,而三军之士皆有饥色。” 莫砺锋先生说:杜甫本是一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人,他对楚庄王攻宋的故事一定十分熟悉。当他想揭露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时,这个典故自会浮上心头,并现于笔端。杜甫晚年作《驱竖子摘苍耳》,其中说“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也是运用同一个典故。《新书》明言“厨肉臭而不可食”,这个“臭”字只能解作“秽恶之气”。莫先生的意见当然是对的,如要精准一点,这里的“臭”理解为“腐烂”可能更好,跟“酒败”相应,都是指食物变质不能吃,强调的是品质而不是气味。“肉臭”也可以说成“肉败”,意思一样。如《论语·乡党》“鱼馁而肉败,不食”就是指不吃腐烂变质的鱼和肉。杜甫诗中的“酒肉臭”显然源自《新书》,也应该指酒肉变质变坏,不一定要臭气熏天![2] [1]有人考证认为“王孙子《新书》”并不存在,所引楚庄王事可能是出自《王孙子》。见“知乎”网“夜小紫”对“如何理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臭’字?”问题的回答。本文权且按照莫砺锋先生的引用来说话,因为无论出自那里,只要语句客观存在且在杜甫之前就不影响结论。 [2]汪少华,邓声国:《也谈“朱门酒肉臭”的“臭”》,《古典文学知识》年第5期。 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伤宅》也用了《新书》典故,而且明显受到杜诗的影响,可以看做是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意的具体化: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虚且迥,坐卧见南山。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其中的“臭”跟“败”同义连用,跟“朽”对用,不过“朽”的并非“钱”,而是串钱的“贯”,所以最好把“臭败肉”跟“贯朽钱”看作整体对用。清谭嗣同《仁学》“宁使粟红贯朽,珍异腐败,终不以分于人”也是语义的整体对应,“臭败”换成“腐败”,“臭”的腐烂变质义更是确切无疑。 但问题是,《新书》的“肉臭”和“酒败”是分开说的,杜甫为什么要合在一起说成“酒肉臭”呢?正如香气方所质疑的:“肉能臭,酒也能臭吗?”酒是越陈越香的,那这个“臭”管得住“酒”吗?白居易不说“酒肉臭”而改说成“臭败肉”,也许正是为了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肉”的腐烂既可以说“臭”也可以说“败”。 这个问题不是新提出来的,所以臭气方已经有不少人作了回答。有的认为“酒肉臭”实际上只是“肉臭”,“酒”是“连类而及”的无义成分,或者“酒肉”按“偏义复词”看待,其中的“酒”也是无义的。[1]但无论从语源看(《新书》中“酒肉”都是有义的),还是从事理看(朱门里为什么只有肉没有酒?),这种排除“酒”义的解释都是无力服人的。有的认为“酒也能臭”,所以能够合说成“酒肉臭”,理由是唐代以前没有蒸馏水烧制的白酒,只有米黍等酿制的黄酒。黄酒浊度大杂质多酒精度低,很容易变酸变臭。[2]这是用酒能否变质的事实作答,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客观事实跟语言表达并不一定完全合辙,即使黄酒确实能够变臭,古人就一定会用“臭”来表述这个事实吗?根据语料调查发现[3],唐代以前表述酒变质变坏一般说“酒败”“酒酸”,“酒败”已见上,“酒酸”如《焦氏易林》:“行作不利,酒酸鱼败,众莫贪嗜。”而“酒臭”通常是指酒的气味,可能并不好闻,但没有变质、臭气的意思,也不特指香气。如: 《韩非子·十过》:“子反之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绝于口,而醉。战既罢,共王欲复战,令人召司马子反,司马子反辞以心疾。共王驾而自往,入其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醉如此,是亡楚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不谷无复战矣。’” 子反醉酒称病,楚共王去他的营帐探视,闻酒气而知实情。下面的“酒臭”用例也是很典型的表“酒气”义,因为它们都不是对“酒”的陈述或形容,而是某人或某物散发出的酒气,“酒臭”的“酒”起区别作用: 晋葛洪《神仙传·栾巴》:巴为尚书,正旦,会群臣,饮酒,巴乃含酒起望西南噀之,奏云:“臣本乡成都市失火,故为救之。”帝驰驿往问之,云:“正旦失火时,有雨自东北来,灭火,雨皆作酒气也。”宋《册府元龟·总录部·方术》引作“雨皆酒臭”。 南朝刘义庆《幽冥录》:会稽郡吏鄮县薛重得假还家,夜户闭,闻妻床氏有丈夫眠声。唤妻久,妻从床氏出,未及开户,重持刀便逆问妻曰:“醉人是谁?”妻大惊愕,因苦自申明实无人意。重家惟有一户,搜索了无所见,见一大蛇,隐在床脚,酒臭。重便斩蛇寸断,掷於后沟。 《太平广记》引《五行记》:义宁初,一县丞衣缨之冑。……其后沉湎于酒,老而弥笃。日饮数升,略无醒时。得病将终,酒臭闻于数里,远近惊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此人遂卒。故释典戒酒,令人昏痴。今临亡酒臭,彰其入恶道耳。 [1]杨春霖:《“朱门酒肉臭”释义辨正》,《古汉语研究》年第2期。 [2]尹戴忠,赵孜:《“朱门酒肉臭”的“臭”字释义争议及辨正》,《语文知识》年第1期。 [3]参考BCC语料库和CCL语料库。 用“酒臭”表示“酒气”一直延续到清代。如: 《聊斋志异》:醉人益怒,捉袂使不得行,酒臭熏人。 《红楼梦影》:这里袭人同五儿出来,说道:“这是怎么说,找到屋里来惹气,快卷起帘子出出这酒臭。” 《镜花缘》第九六回:正朝前走,忽觉酒气熏人,忙掩鼻道:“那里来的这股酒臭!” 在能够检索到的近个用例中,只有下面1例的“酒臭”是指跟“香”相对的气味: 北凉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卷二十:“医闻是已,即前嗅之,优钵罗香、沉水杂香、毕迦多香、多伽罗香、多摩罗跋香、郁金香、栴檀香,炙肉臭、蒱桃酒臭、烧筋骨臭、鱼臭、粪臭。” 其实这里的“香”“臭”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香气、臭气,只是医者从病人身上闻到的各种具体气味,并按照佛家的思想大别为两类而已,凡植物花草即为“香”,凡酒肉之类佛家禁忌的食物即为“臭”。实际上等于说在病者身上闻到了优钵罗花的气味,……,闻到了蒱桃(葡萄)酒的气味,……,甚至大便的气味。可见“香”“臭”都是泛指气味,是佛教意念上或情感上的香臭,不是特指的“香气”和“臭气”,因而“蒱桃酒臭”不能理解为葡萄酒变坏发臭了。 《新书》的语源只能证明“肉臭”的“臭”是腐烂变质(或发臭)义,黄酒容易腐败变质也只能证明有此客观事实,都无法解释清楚杜甫“酒肉臭”的语言表达理据。因为就用词习惯而言,如果要表达酒的变质发臭,杜甫应该不会使用“臭”字,而且杜甫之前并没有“酒肉臭”合说的先例,那怎么会出现“酒肉臭”这样的表达形式呢,这样的表述符不符合汉语的表达规则呢? 我们认为杜甫采用“酒肉臭”的表达形式,固然跟诗歌的语言局限有关,但并非要用“臭”分别对应“酒肉”表达“酒臭”“肉臭”,就是说并非语言发展到唐代酒水变质发臭就可以说“酒臭”了。事实上唐代以后仍然习惯于用“败”来表述酒类的变质,如: 唐李世民《赠魏徵诗》:“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瓒。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唐崔护《山鸡舞石镜》:“何言资羽族,在地得天倪。应笑翰音者,终朝饮败醯。” 唐元稹《春六十韵》:“饮败肺常渴,魂惊耳更聪。” 清钮琇《觚剩》:妇曰:“吾绝粮已久,安所得粟?忆君去后,犹存故人酒一罂。请佐君软饱可乎?”妇往邻家觅薪,李即发罂。罂内产一芝如盘,紫光煜煜。喜且愕曰:“此瑞徵也,顾酒败不可饮奈何?” 清沈季友《檇李诗系》:“朝莫盼武陵花,夕莫饮乌程酒。武陵花谢乱人心,乌程酒败伤人口。” 那么,如果杜甫在用典时要取一个词来对应“酒肉”两个事物的话,应该选择“败”才是,因为酒变质可以说“败”,肉变质也可以说“败”,可是杜甫选用了一般不表示酒变坏的“臭”,那么这个“臭”就应该不是针对“酒”的。我们认为,“酒肉臭”应该是“酒败肉臭”的并言省文。这种并言省文现象在汉语中并非孤例,古代学者早有论述。如: 唐孔颖达《左传·襄公二年》“以索马牛皆百匹”正义: 《司马法》:“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则牛当称“头”,而亦云“匹”者,因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经传之文,此类多矣。《易·系辞》云“润之以风雨”,《论语》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车马”,皆从一而省文也。 宋代王楙《野客丛书》: 《论语》:“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乃因脯而并言。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系辞》“润之以风雨”,《左传》“马牛皆百匹”,《玉藻》“大夫不得造车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言之体,不可不知也。 清王引之《经义述闻》: 《左传》:“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杜注曰:“亨,通也。”陆粲附注曰:“刘向《新序》援此文,亨作享,古字亨享通。”引之按:亨当从《新序》读为享,杜不读为享者,盖以神可言享,人不可言享耳。不知古人之文,多有从一而省者,人固不可言享,亦得因神而并称之。《襄二年传》:“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因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经传之文,此类多矣。《易系辞》云:“润之以风雨。”《论语》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车马。”皆从一而省文也。然则“以享神人”,亦是从一而省文耳。 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二第十五条引孔颖达《正义》之说而按: 此亦古人行文不嫌疏略之证。使后人为之,必一一为之辞:曰“以索马百匹,索牛百头”,曰“沽酒不饮,市脯不食”。此文之所以日繁也。 就是说,“马牛皆百匹”是“马百匹,牛百头”的并言省文,“润之以风雨”是“润之以雨,散之以风”的并言省文,“沽酒市脯不食”是“沽酒不饮,市脯不食”的并言省文,“不得造车马”是“不得造车,不得养马”的并言省文,“以享神人”是“以享神,以化人”的并言省文。这种表达现象还有别的用例,甚至在现代也还存在,如《墨子·非攻》“入人园圃,窃其桃李”可理解为“入人园窃其桃李,入人圃窃其菜蔬”的并言省文;《青藏高原》歌词“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一座座山川相连”实际上应该是“一座座山,一条条川”的并言省文。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杜甫诗的“酒肉臭”实际上就是《新书》“橱肉臭,尊酒败”的并言省文,这样就不存在“酒”有没有意义,“臭”跟“酒”能不能搭配使用之类的问题了。 顺便说一句,这种并言省文的表达现象被清代学者阎若璩混同为“连类而及”,现代人以讹传讹,也都按照“连类而及”或“偏义复词”的思路错误地理解上述辞例,是需要我们纠正的。详参李运富《论意域项的赘举、偏举和复举》(中国语文年第2期)。 二、杜甫之后的“酒肉臭” 或因误解而变“香”义 杜甫的这两句诗对后世影响很大,仿作和化用者很多,由于各自的理解不同,导致“臭”的意义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认为后世所用的“酒肉臭”就等于杜甫的“酒肉臭”,因而可以用后世的“酒肉臭”来推证杜甫“酒肉臭”的实际含义,那在方法论上是不可取的。 仿作或化用者有的跟杜甫原意保持一致,如前举白居易的“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再如: 宋李处权《简柴端叟》: 笔端落落曳十牛,老气飘飘横九州。河伯未睹北海若,鲁人未识东家丘。豪户但余酒肉臭,要涂只益衣冠羞。旦评公议百年后,此士斯文班马俦。 前后诗句都是负面设词,“酒肉臭”也只有理解为负面的腐臭义才能协调。 宋吴则礼《江边简新之》: 楚郎天生五车书,以锥画沙绝世无。穷年饱吃衲子饭,粱肉臭腐宁关渠。 这个腐臭意义明显,虽然不能断定出自杜诗,但至少是类似。 用这些材料来证明杜甫的“酒肉臭”确实是腐烂发臭当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也有人能够举出反例,比如王晓祥《“床前明月光”新解》》(语文园地.5)谈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认为其中的“臭”字解为“飘香”为好,理由就是唐元稹《估客乐》写过“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的句子,意思是商贾用酒肉收买门卒,给胥吏修建新房。“市卒酒肉臭”是当时饮宴之情,其中的“臭”解为“飘香”是肯定无疑的,那么杜甫的“朱门酒肉臭”也应该是朱门内宴饮酒肉飘香之意。 又如程耀恺《被误解的名诗》(中国食品.10)说:“明代诗人叶敬平于某年正月去拜访友人,他写道‘未进君家门,先闻酒肉臭’(笔者按,未查到原文),可知所谓‘酒肉臭’,实际上是指酒与肉发出的香味飘溢于空气之中。所以,杜甫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实为‘豪富府中飘出的是酒肉的香气,而路途上却是冻饿而死的穷人’。” 其实杜甫之后用“臭”来表述酒肉之香的还不只元稹、叶敬平,下面的用例也是: 宋黄庭坚《以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为韵寄李子先》: 穷阎蒿蔓膻,富屋酒肉臭。 酒肉令人肥,蒿蔓令人瘦。 这里“穷”对“富”,“膻”对“臭”。“膻”是不好闻的气味,那“臭”应该就是好闻的气味。而且下文说“酒肉令人肥”,显然是从正面立言,不会是指腐臭的酒肉。 清李銮宣《坚白石斋集·卖子谣》: 老父谓儿女,卖汝乃爱汝。 朱门酒肉臭,但去无所苦。 不想让儿女在穷人家挨饿受苦,所以把儿女卖给富人家,好去享受“朱门酒肉臭”,那当然是指酒肉香。 清杨恩寿《词余丛话》: 《空谷香》云:“一答山川邪秽,琼花开后古风微。耳靡靡诗传《郑》《卫》,眼梦梦世降陈隋。掘邗沟流一派桃花当户水,煎碧海簇几处赤甲白盐堆。灯摇得绮罗香墙张锦绣,风吹来酒肉臭犬餍甘肥。” 甘酒肥肉,阵阵香气被风吹来。 面对上述用例,主“臭气”说者内心是崩溃的,他们只能强辩这些“臭”仍然只是指“气味”而不是“香气”,或者干脆把“市卒酒肉臭”解释为市卒送给商人的酒肉多得发臭了,以维护杜诗“臭气”说。但显然论证乏力,难以解释上述语境。 虽然很多学者已经证明杜甫之前的“臭”并没有“香气”或“香”义,那些被解释为“香气”的用例大都似是而非,值不得推敲。[1]但杜甫之前的“臭”没有“香气”义,并不等于杜甫之后的“臭”不能解释为“香”或“香气”,上述语境中的“臭”确实是指“香”或“香气”而言,即使理解为“气味”也是偏重正面的好闻的诱人气味,无需强辩。那么这些“臭”的“香”义是怎么产生的呢,能不能用来证明杜诗的“酒肉臭”也是“香”呢?我们认为这些仿用或化用杜甫诗句的“酒肉臭”之所以会有“香”或“香气”义,并非词义的自然引申(在有“香”词的情况下要把“臭”引申为“香”是没有必要的),而应该是误解杜甫诗句并加以仿用的结果,因而不能反过来证明杜甫的诗句也是这个意思。 前面已经论证,杜甫诗句源自《新书》,本来就是取的“腐臭”义。但由于诗句字数和格律的限制,杜甫采用了“并言”“省文”的表述方式,把“酒败”“肉臭”合并说成“酒肉臭”。而后人既能知道杜诗语句出处又能体味并言省文表述方式的决不会太多,如果不懂得杜诗的来龙去脉,又看到前人在别处有“臭,香也”之类的随文释义,就很容易误会杜甫诗中的“酒肉臭”就是“酒肉香”,并且按这种误解模仿使用,从而就出现了上述真的要按“酒肉香”来理解的诗文。 无独有偶,不仅有把“臭”误解为“香”而出现的仿用,而且还有虽然“臭”仍是腐臭,却因不明杜诗的“省文”手法而误解“酒臭”相配的,如 宋代石介《彼县吏》: 嗟乎嗟乎彼县吏,剥肤椎髄民将死。夏取麦兮秋取粟,笞匹红兮杖匹紫,酒臭瓮兮肉烂床,马馀梁兮犬馀气。雀腹鼠肠容几何,虎噬狼贪胡无已。 “酒臭瓮”当然是指酒在瓮里变质酸臭,前面说过,古人表述酒变质的意思通常用“酒败”“酒酸”而不说“酒臭”,宋代的用词搭配情况也是如此。而石介可能不明杜甫的“酒肉臭”是“酒败肉臭”的并言省文,以为杜甫说的是“酒臭”和“肉臭”,所以也跟着说“酒臭”“肉烂”了。 这种因误解前人原意而产生新词新义的语言现象应该不在少数,积非成是也许是语言发展演变无法回避的一种事实,但绝不能用“非”来改“是”,不能把“是”变成“非”。即使不属误解,后世化用时有意改变原典词义和用法的情况也不能排除。总之,词义因各种缘故发生变化是正常的,误解原意也是产生新词新义的一条途径。[2]误解误用可以成为解释新词新义的理据,但不能反推被误解的词语词义必须按新词新义来理解。所以用“市卒酒肉臭”和“先闻酒肉臭”之类的后世新用法来反证杜甫诗句原意的做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1]唐钰明:《“臭”字字义演变简析》,《广州师院学报》年第3期;赵川兵:《“朱门酒肉臭”之“臭”字解——兼谈“臭”字解法的应用》,《苏州科技学院学报》年第6期。 [2]李运富:《从成语的“误解误用”看汉语词汇的发展》,《江苏大学学报》年第3期。 (本文转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年第5期,引用请据原刊。) 微刊投稿:hanzixueweikan .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ongyaozia.com/hyzyll/10390.html
- 上一篇文章: 当代诗词大家精选系列之周燕婷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