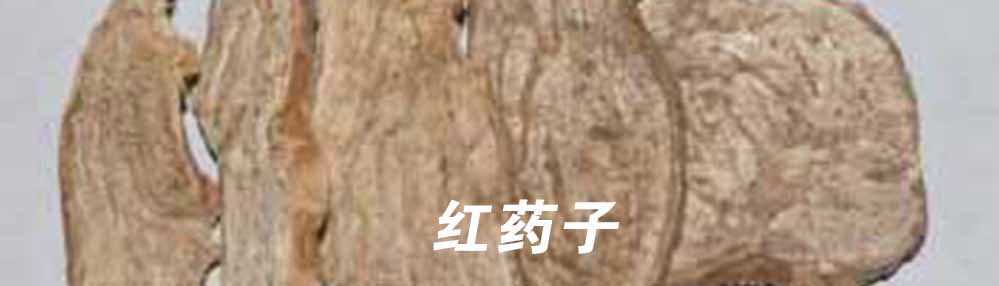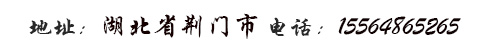书楼个园藏书楼的名称应当叫汉学堂上
|
个园是我的寻访计划之一,这次我要弥补上次寻访中的失误。十几年前,我曾来到个园,那时目的是为了寻找扬州二马的藏书楼——丛书楼,当时个园已经是扬州著名的旅游景点,门票好像是十元,买票之后一路走一路打听,直走到个园的最深处,才找到丛书楼,记得里面是个商店,游客也不少,匆匆拍了几张照片离去。 近些年仍在查找着各种藏书楼的资料,随着网上资讯的增多,现在寻找藏书楼的资料比以往方便了许多,虽然网上的资料有太多的错漏,但毕竟可以提供一些线索,沿着线索一路查下去,多少能找到些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我的这种搜索所得之一,是发现自己当年在个园之中寻找到的藏书楼跟扬州二马关系不大,这里面的历史延革较为复杂,《扬州画舫录》中有这样一段话,“佩兮于所居对门筑别墅曰‘街南书屋’,又曰‘小玲珑山馆’,有看山楼、红药阶、透风透月两明轩、七峰草堂、清响阁、藤花书屋、丛书楼、觅句廊、浇药井、梅寮诸胜。玲珑山馆后丛书前后二楼,藏书百橱。” 我从此门进 这里的佩兮是马曰璐的字,这段话关键之处在于“于居所对门”,也就是说街南书屋和小玲珑山馆并不是扬州二马兄弟的住所,而是别墅里建的藏书楼,我仔细寻找,本来就打算去个园,但我在东关街上寻找的是街南书屋,无意中看到了街南书屋的斜对门就是个园的后门,如此看来,这应当是古代时原有的格局,因为个园就跟街南书屋隔一条窄窄的小街,而应当是一种方位上的实写,书屋就在街道的南面嘛。如此推论起来,现在的个园应当是扬州二马的居所。 东关街号就是个园的后门,门口同样立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铭牌,而另一侧墙上立着一块木制的像屏风状的布告栏,这里面写的却是“个园黄氏家联”,家联里写着“数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有良图惟俭与勤。”不知道为什么,将这前后不搭的两副对联写在这里。从后门进入,门票是50元,入门处停着两三辆人力三轮,一直阻止我从此进入,告诉我进个园一定要走正门,他要把我拉到正门去,十几年前我访个园时就是从正门进入的,没觉得省了什么事,今天我想走后门,他为什么要阻止我呢。 不知道为什么把对联写成这样 进入园内我才知道自己选择的正确,因为最后一处院落正是我的主要寻找对象——汉学堂。汉学堂是个园主人黄至筠二儿子黄奭的藏书楼,从外观看汉学堂并不起眼,而里面布置得却别有洞天,其中的侧房专门做成了展室,由展板的形式介绍着黄奭的生平及其交往,其中一个展板上写着这样一段话,“黄奭将一生精力献给了古书辑佚事业,黄家藏书丰富,黄奭本人勤奋好学,对于辑佚古书精益求精,校仇精审。他在辑佚方面的成就,与同时代另一位学问家马国翰齐名,称为‘辑佚两大家’,《清史列传》卷六十九中有黄奭传。”这句话概括了黄奭一生的事业所在,同时指出了黄奭在辑佚方面的成就是来源于他家藏书的丰富,只是这里所说的“校仇精审”的“仇”字似乎写作“雠”字更为专业。 汉学堂藏书楼的正门 个园主人黄至筠是清代嘉道间两淮盐商的“首总”,这个地位绝对可以称得上富可敌国,汪鋆在《扬州画苑录》中评价黄至筠说“幼即以盐策名闻天下,能断大事,肩艰巨,为两淮之冠者垂五十年。”他竟然是扬州五十年没有改变地位的第一大盐商,可见其家财要比扬州二马大许多,发家之后,他逐渐买下了扬州广储门一带大片地产,具体多大面积我没查到,只是找到了这么一句形容词——“甲第连云”。黄至筠共有妻妾十二位,生有十三个子女,这些子女计有五男八女,按照历史记载他有四个儿子,经过近代学者不断发掘,最后把他第五个儿子的名字也找到了,黄至筠的十二位妻妾中其中一位是朱氏,朱氏一共育有二男一女,而黄奭是朱氏所生长子,黄奭在黄至筠的五个儿子中排在第二。 汉学堂 黄奭应当是黄至筠的子女中最有学问者,他的学问一边来自于天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黄至筠对他的重点培养,他给自己的二儿子聘请了许多那个时代一流的学者为其师,比如嘉庆二十四年拜曾燠为师,而曾是当时天下以文章名世者,嘉庆二十五年拜吴鼒为师,道光六年又拜江藩为师,这几位都是著名的经学大家,到晚年又拜阮元为师,虽然说是晚年才见到阮元,其实黄奭仅活了四十四岁,除此之外,黄奭还跟刘凤诰学制艺,跟吴兰雪学诗,跟王城学篆刻,跟陈逢衡学校雠,看到这么多名师能够教其一人,真让我叹羡。 阮元与黄奭交往故事 汉学堂旁的这间展室里面有一段是阮元跟黄奭交往的故事,这间展室旁边的一间厅房悬挂着一个匾额,上书“勤博”二字即阮元所书,而这二字正是阮元送给黄奭者。得此二字的来由据说是道光二十二年的某日黄奭邀请阮元、梁章钜等名家来个园赏芍药,赏芍药之余,黄奭给众人出示了一方宋代名臣文天祥所用的砚台,此砚叫“玉带生砚”,因为是名人旧藏之砚,引起了众人的兴趣,而阮元恰好也带来一方端砚,他就把这方砚台送给了黄奭,黄奭很是高兴,专门请人绘制了《授砚图》。 侧厅中阮元题的匾额 关于这方“玉带生砚”,徐珂的《清稗类抄》中有如下记载,“玉带生砚,乃端州产,石质非上品,以砚有白线一痕,故名,为宋文天祥故物,谢叠山、黄石斋均曾宝藏。道光时,归吴人某。同治时,粤寇李秀成陷苏州,颇嗜书籍古玩,亦珍储之。合肥李文忠公克苏州,得此砚,传三世。后藏伟侯袭侯国杰家。” 徐珂这段话记载的是这样一段故事:其实玉带生砚最初是南宋诗人刘辰翁所用,后来刘辰翁把这方砚台赠送给了文天祥,宋景炎二年,文天祥又把这方砚台转赠给了谢翱,谢翱去世后,葬于浙江严子陵钓台,至此之后,玉带生砚不知下落。到了元至正十六年,杨维祯前来严子陵钓台凭吊谢翱时,在荒冢中发现了玉带生砚,元末战乱,又使得这方砚台不知下落,直到清康熙年间,宋荦才又买得此砚,后此砚传入宫中,被乾隆皇帝藏于三希堂内,弘历很喜欢这方砚台,专门写了一首“御制玉带生歌”,并且把这首诗刻在了玉带生砚的背面。此后的递传情况就不清楚了,若按上述徐珂的记载,在道光年间归了吴某人,何时从宫中传出到了吴某人手里,却未见记载。徐珂说同治年间,李秀成在苏州得到了这方砚台,后来李鸿章打下苏州后,砚台又归了他,这段有意思的递传使这方砚台成了名物,现在的这方玉带生砚藏在了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原物我没有看到过,但曾经看到过图片,那方砚的形象就象是一个人光着脚踏在泥上印出的脚印,并看不出有何稀罕之处,可能更多的原因是这方砚台经过了那么多名人的递传吧。 阮元官服像 在这个递传故事中,我没有查到这方砚台何时到了个园的记载,但玉带生砚的确曾藏在个园,对于这个递传有兴趣知道来龙去脉者并不是我一个人,当时梁章钜就曾给黄奭写了封信,信中说“玉带生真砚,风闻归阿鹾使,未知尊斋所藏,即从彼得来否?暇日尚容捧观”,我不知道黄奭当时给梁章钜的回信中是否提到了他家是如何得到这方砚台的,如果能发现这封信就能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圆满,上面徐珂所言道光时归了吴某人,不知道是不是指的黄奭去世之后,此砚流出之后的递传过程,但总之,这些递藏中总有多个断环不能将其连接起来。 这个堂号街南书屋里也有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ongyaozia.com/hyzcf/10662.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天学中药沉香
- 下一篇文章: 运河故事运河为什么是铜帮铁底